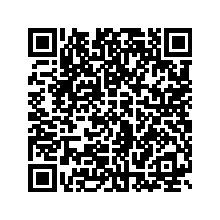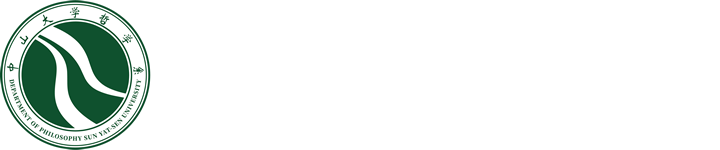“哲学前沿”课程讲座第十六讲纪要|潘大为:理解文科:人文学科的概念及其中国影响
2024年6月19日晚,抢庄牛牛-抢庄牛牛规则 2023级研究生“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六讲在锡昌堂103举行。本次讲座由抢庄牛牛 潘大为副教授主讲,主题为“理解文科:人文学科的概念及其中国影响”,抢庄牛牛-抢庄牛牛规则 副教授李长春主持讲座。
讲座开始,主持人李长春老师介绍了主讲人潘大为老师的研究方向,指出潘老师有文、理、医跨学科背景,其研究涉及医学哲学、科学哲学、比较哲学等方面。
潘老师在现场同学的期待中开始了今晚的讲座。“文科有什么用?”“文科与理科有无高下之分?”“文科生是已经太多,还是远远不够?”潘老师提出,这些问题是文科学生在会在求学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反映出公众对文科专业的理解。这些问题实际上和大学文科教育的职业出口规划不清晰有关。读医科的职业导向是医生,读工科的职业导向是工程师,但文科专业的职业导向相对而言不那么明确,哲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科教育为什么会与当今社会脱节,潘老师给出了四点原因:一、传统文化,即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引入科学和民主的概念,现代科学地位上升,人文地位下降;二、建制因素,即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受到前苏联的巨大影响,文理分科,专业划分过于固定而且过细;三、教育经济学,主要指二十世纪末中国大学扩招,高等教育普及化也导致就业形势发生变化;四、语言多样性和哲学翻译,即中文语境下文科定位模糊,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西方学术传统的相关概念的中英混译的混乱现象,且对语言和思想的复杂关系未给予充分重视。
想要回答上述问题,潘老师建议,我们首先要明确文科的定位,这又要求我们从历史维度去理解文科的演进轨迹。她指出西方教育有着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于古典学术的古典教育,即科学革命前的人类知识形态及传播方式,可分为自由教育、中世纪大学教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三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基于现代学术的现代教育。以地位和占比不断提升的科学教育为突出特征,是当前全球范围内工业社会的主流教育模式。
潘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西方古典教育的三个阶段。自由教育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公民教育,即城邦自由民参与公共事务,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所需要的全人教育。就其服务对象而言,它从一开始就是为社会上层人员提供的精英教育,不是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大众教育。这种教育也不是象牙塔式的教育,而是紧贴当时社会知识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的心智训练。中世纪欧洲大学教育以古典“自由教育”中的七艺为基础。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基督教化,即与天主教义相融合,二是“三艺”地位的上升。潘老师以明末来华传教士艾儒略《西学凡》内容为例,介绍了当时欧洲教育内容:“文科”即修辞学,是大学教育的第一个基础阶段,“理科”指哲学,在修辞学之后教授。完成四年的文理教育后,学生则进入神学或世俗专业教育(主要指法律和医学)。从艾儒略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教育被视为专业教育的前提和基础,这与当今大学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理念相似。文艺复兴后,在崇古思想的推动下,意大利学者首次提出了“人文学”的概念,其内容奠定了后来西方人文学科的基础。相较于前面两个阶段,“人文学”有着两个方面变化:第一,重视对古典语言和文献的修习;第二,更强调“三艺”中情感性、文学性的内容,即修辞和语法,而相对弱化形式化、理性化的逻辑学内容。这两方面的变化也贯穿了西方近代以来人文主义的传统,并持续体现在当代西方人文教育中。
在西方思想中,有一个悠久的二分法:“神圣知识”(拉丁文scientia divina,英文divine knowledge或divine science,也可称神圣科学)和“人类知识”(拉丁文scientia humana,英文human knowledge或human science,也可称人类科学)。我们在使用“科学”这一中文词汇时,实际上有着两种含义:一是分科之学;二是现代科学。潘老师认为,翻译过程中不同语言背后内涵的缺失,也是当今中国理解文科与科学关系出现混乱的重要因素,我们有必要对“人文学科”这一概念进行梳理。
潘老师以英、德、法三种主要近代学术语言为例,介绍了“人类科学”概念在翻译过程中的内涵变化。首先是从英语到德语的翻译,十七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大发展使人们期望将科学方法延伸用于处理人类心理及社会现象。这催生了近代欧洲知识界关于“道德科学”“人类科学”的讨论。苏格兰经验论哲学家的用词就开始明显受到科学的影响,如洛克的“人类科学”(human science)、休谟的“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后来德国学者狄尔泰使用“精神科学”一词(Geisteswissenschaft)翻译休谟“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词语在翻译的过程中,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休谟所用的概念反映的立场是可以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人类精神,狄尔泰所用的概念传达的立场则是人类的精神不应被科学化。法语使用“人类科学(sciences humaines)一词,其内涵受到法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可被视为经验主义哲学的一个强版本,在实践层面则要求是把自然科学对物质世界的研究方法直接扩展到人类对象上去。
当代英语世界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从两个方面继承了以往的传统:一是对古典语言和经典的推崇,一是对数学、逻辑性等形式化知识的疏离,这也决定了它在面对现代科学受冲击的方式。潘老师以“古典学”为例,讲述了英语世界的人文学科的变化。古典学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曾经在西方学术中有崇高的地位。但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它在西方人文学科的内部地位不断下滑,成为了一个小众学科。美国哲学家杜威就曾对古典学科进行过直率的批评,认为古典学过度重视希腊与拉丁文,与现实脱节。潘老师并指出,就现实来看,当代西方的文科教育在经受严重危机,大学文科经费和教职不断缩减,文科毕业生的工作机会也不容乐观。
二战之后,学术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英语文化对当今世界的知识图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英语世界将所有的知识分成三个领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科建制也按照这种分法展开。这一区分直接导致人文学科被排除在现代科学之外,而随着现代科学知识和影响的爆炸性增长,人文学科领域相对萎缩。在这一时期,人文学科(humanities)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法、德语境下的“人文科学”概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情况也影响了汉语学界在“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使用上的区别。近三十年来汉语学界的一个重要的用词变化是,“人文学科”概念逐渐成为主流用语,“人文科学” 词逐渐失去其昔日的影响力。“人文科学”一词更多地见于老一辈、尤其是对德国哲学传统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年轻学者,特别是有英语学术训练背景或系统科学训练的学者则更多地使用“人文学科”概念。
在讲座的最后,潘老师总结说,“人文学科”的概念史,也是人文学科面对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的冲击,持续反思自身的前沿与限制的历史。这也要求我们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有没有一些思考的方式是不能被现代科学所覆盖的,并且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二是如果我们不认为科学范式是唯一可行的研究范式,那么人文学者应该用什么范式去做研究?
潘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提供了一种解题思路:科学与人文的确不一样,但这种不同并不是一种对立,文理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去寻求一种科学与人文交叉融合的新研究范式。潘老师强调,这一问题的解题思路并不唯一,也不是固定的,所有同学都可以有自己的思考,去寻找现代社会文科的价值所在、不可替代性所在。
互动和交流
在互动与交流环节,李长春老师首先总结了潘老师讲座的特色,一是用严肃的思考去审视了同学们切身相关的问题;二是注意语言和思想的对应性,注意语言在翻译、流传过程中背后含义的变化。紧接着李长春老师对讲座中的几个概念进行了补充:首先,李长春老师指出大学是教育人的地方还是研究科学的地方,这一问题的答案并没有定论。前一种理解和人文密切相关,后一种和科学密切相关。随着二战以后美国政治经济地位上升,美国的高等教育往往被视为标杆,对科学的重视也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得到了贯彻,并得到了推广。这也导致了当今世界存在欧式与美式大学教育的区别,这两种教育偏重各有不同。再者,李长春老师认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学者随着对西学研究的深入,也出现了反思近代唯科学主义的思潮。这一反思的结果使得人们重新思考人文学科的价值,从对科学的崇拜解放出来。最后,李长春老师给出了他本人对古典学的理解,西方古典学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文明典范,这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的古典学则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其他古代文明,进行诸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
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